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狄马:宠辱皆忘是一种风度吗?
利季娅,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俄罗斯文学专家蓝英年说,他是直到1989年才知道她的,我是前几年看了蓝英年先生的《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才知道她是苏联有名的小说家、散文家。
1939至1940年,利季娅写出了反映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但没有哪家出版社肯冒死出版。苏共二十大后,当局开始反思斯大林时期的铁腕政策和“个人崇拜”,利季娅把小说投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总编看了很高兴,决定立即开印并预付稿酬。谁知没过多长时间,上面就改变了想法:认为文学作品还是要多谈成绩。
既然党已经意识到了错误,并给一些镇压错了的人恢复名誉,就不要再揭伤疤了。利季娅被重新请到编辑部,先前那个赞赏有加的总编这时判若两人,他说:“我一开始就对您说,您的小说在思想上是有害的。”小说是出版不了了,但利季娅把出版社告到法院,法院让出版社支付了全部稿酬。
利季娅从此知道当局的意图就是让屠杀和镇压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果及时封住报刊的嘴,最后等到受难者和见证人统统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发生过的事,不能从祖辈和父辈的经历中吸取任何教训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铲除记忆的常见办法是用谎言掩盖现实,实在掩盖不了时,就用某某某代替死者的名字,用“悲惨地中断了自己的生命”代替大镇压时的秘密处决。利季娅决定与这种有计划、有目的的遗忘战斗。她说:“就算不再发表我写的一个字,就算我所呕心沥血的文学构思永远无法实现,也决不允许任何人从我作品中删除牺牲者的姓名和导致他们牺牲的共名。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休想。”
作家协会一直想整她,却苦于找不到借口。1973年全国的报刊疯了似地攻击索尔仁尼琴和萨哈啰夫,甚至一些她所尊敬的作家和院士也加入到了这些疯狗的行列。利季娅写了一篇戳穿谎言的文章《人民的愤怒》交给了美国之音的记者。作协终于找到了整治她的口实。
1974年1月9日她被召到作协大楼会议室,帕斯捷尔纳克就是在这间会议室里被开除的。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几乎失明,但开会时仍然夹着一摞白纸走进了会议室。一群男女轮番发言,极尽表演之能事。有的对她表示愤怒,结果心脏病复发,昏厥过去;有的说看了她的文章伤心,假装哽咽说不出话来。结论是事先就定好的,无非说她的作品是“反苏、反人民”的。会议一致通过开除了利季娅的作协会籍。她说“克格勃和作家协会是兄弟单位”,其实在极权体制下克格勃的兄弟单位很多,何止作家协会?
好在过了15年,即1989年2月,俄罗斯作协通过决议,撤消了1974年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利季娅又重新成了作协会员。又过了两年,这个用尸骨和眼泪充起来的帝国就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了。正如西谚所云:正义敌不过权力,权力敌不过时间。利季娅在开除她的会议上用颤抖的手记下的每个人的发言,成了研究极权政治对知识分子灵魂扭曲、瓦解的重要资料。透过这幅作家们为保住官位或巴结权贵,不惜出卖良心,背叛师恩,甚至落井下石的“群丑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极权统治是如何通过每一个软弱而无耻的人来实现它的计划的。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度,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其实是很淡薄的。在一场场我们倍感亲切的发言与会议中,有谁像利季娅一样如史家般严谨地记下当时的每一声泣哭,每一句攻击?秦的焚书坑儒,汉的罢黜百家,明清两季此起彼伏的文字狱当然远了,20世纪下半叶的故事总不会没有人记得了吧?在多如牛毛的运动中是谁制造了那些骇人听闻的冤狱和流血?不要给我说是“罪恶的时代”,“极左路线”。
时代是谁?路线又是由谁制定,通过什么人执行的?他们在哪次会议上有污人清白、揭人隐私的讲演?在哪场批斗中有大打出手、致人死地的壮举?这些导致成千上万人饿死、瘐毙或被抓、被杀的惨剧当初是由什么人签署,事后又有多少人得到了惩处?当我们在各种回忆文章中自觉地为他们隐去姓名,用×××代替时,我们何尝意识到我们自己就是集体谎言和集体遗忘的同谋?
赫尔岑说“凡是不敢说的事,只存在一半。”只存在一半的事,后人怎么师法?怎么借鉴?我们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前事连一个完整的记录都没有,怎么能“不忘”?又谈何“师之”?中国人也许是经历的苦难太多,太深了,因而对记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正因为对记忆的恐惧是如此强烈,所以“宠辱皆忘”才被视为一种风度,但这风度提倡得久了,大家就都去追求“皆忘”,而谁也不去问为什么要宠,为什么要辱?于是宠者常宠,辱者常辱;被宠、被辱者也因为“皆忘”而悠然自得;两厢受益,时人谓之“双赢”。
实在忘不掉时,还可以念动另外的符咒:比如“唾面自干”,比如“沉默是金”,比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而这些祖宗的符咒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念起来琅琅上口,但一到现实中就成了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而且更要命的是,念得久了,大家就都去做缩头乌龟,谁也不想从改变制度、环境上用力。比如把“卒然临之而不惊”当成一种制胜法宝口传心授时,大家就都去追求“不惊”,而谁也不去问为什么要“卒然临之”?把“无故加之而不怒”写成条幅到处张挂时,大家就都去追求“不怒”,而谁也不去问为什么要“无故加之”?因为大家都不问,所以“卒然临之”、“无故加之”就成了零成本。
既然我“卒然临之”你连惊都不惊,“无故加之”你连怒都不怒,那我为什么不把“卒然临之”、“无故加之”常态化、制度化?其实苏轼的这两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而我们知道,有这一句和没有这一句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这一句,就说明先前的忍辱负重是为了后来更大目标的实现;而没有这一句,就纯粹成了自欺欺人。即使真做到了,那又和泥塑木雕有什么区别?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不死的中国人都漂去了三亚
意大利有这样一个关于中国移民者的传闻:虽然在意大利生活了百年,但在当地却见不到任何中国人的葬礼,意大利人眼中:他们只会消失,不会死亡。
作 者:徐凯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箱门没有关好,突然敞开,像下雨一样掉下来十几具尸体……是永远不死的中国人。”意大利黑帮文学《那不勒斯的黑手党》曾这样描述那些在当地“消失”的中国人。
意大利普拉托,随处可见的华人身影和汉字符号让这座欧洲小镇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缩影,当地人把这块中国人居住的地区称为“圣·北京”——从迎来第一批中国移民,到“攻陷”意大利绝大多数纺织批发企业,用了不到30年。
这批移民者中,90%的人来自浙江温州。

当时,意大利的纺织业流传着一个说法——能等三到六个月,需要500到1000件的,去中国工厂买;如果只有两周时间,需要100件的,你就来普拉托。
温州人在普拉托的崛起,好比鲶鱼入槽,终究引发了“小鱼”的不满。
随着意大利失业率逐步上升,当地人对中国移民越来越仇视,“干活太多、藏了很多非法移民、只顾做自己的事、从没见过他们的葬礼。”
他们甚至怀疑,中国的黑帮集团会把死了的中国人的尸体通过轮船运回去,然后再将证件倒卖给新来的中国人以牟取暴利。
为了弄清真相,《晚邮报》和《共和国报》记者欧利阿尼和斯达亚诺,从意大利北部出发,途经佛罗伦萨、罗马和普拉托,他们把一路上的见闻记录下来,整理成小说——《不死的中国人: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
想透过意大利人的眼睛去看看——那些不死的中国人,究竟去了哪里?
普拉托
30年前,温州人最向往的意大利城市,既不是米兰,也不是罗马。而是在佛罗伦萨往东南16公里,一座叫普拉托的小城。
它是上世纪80年代,温州人眼里的掘金天堂。
位于浙江南端的温州,自古交通闭塞,三面环山,往东就是无垠的东海,正如《山海经》中的那句“瓯居海中”。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形,使得温州物产匮乏。生活在这里的人知道,想要富起来,唯有走出去。
如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80年代,温州人发现了普拉托——意大利重要的纺织中心。当时,欧洲浮现的巨大商机让温州人跃跃欲试。
那个年代,15万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个天数。但在温州,当地人却愿意花这笔巨资去购买一张通往意大利普拉托的“船票”。
他们听说,只要你勤劳肯干,在纺织厂做两年就能带着第一桶金回国。
“与英美法的中国移民不同,‘到意大利去’的中国人,不是寻觅别处的生活,而是寻觅财富,离开中国,是为了口袋里有更多钱后再回来。”
来到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幸运的从零开始,不幸的从负数开始。
“为了答谢堂兄把自己弄来意大利,惠芳要给亲戚1.5万欧元作为报酬,显然她没有钱,只能用廉价的劳动力来换——在普拉托的制衣厂,每天工作15小时,做满整整一年。”

| 在普拉托纺织工厂工作的中国女工,Marco Bulgarelli / Gamma-Raphovia Getty Images
从北京一路辗转巴黎,最后落地意大利的宁红,甚至从负3万欧元开始。
“到达法国后,宁红接到了蛇头的电话。对方让她到机场商店买一顶阿迪达斯的帽子,戴着它在商店等候……之后,蛇头把她带到里昂车站,宁红上了一辆宽敞的TGV车,踏上了意大利的居留之路——给一家纺织厂每天工作16小时,一周工作7天。”
这群以温州人为主体的华人成群结队来到意大利,他们省吃俭用,干一切重活、苦活,而且可以兼职干几分工作,全年无休。

到了90年代,在意大利站稳脚跟的温州人开始办厂,从打工仔一跃成为老板。当时,在普拉托地区有6000多家企业注册在中国人名下,每年大约有5亿欧元流回国内。
没人能想到,当初只抱了一个纸箱就踏上意大利的这群中国移民,10年后却带着成摞的现金回到家乡,买下一幢又一幢高楼。而看着他们从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的工人,变成每月收入上十万的老板的意大利人,依旧不知道这些“不死的中国人”最后去了哪儿。
除了温州人的“移民潮”,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土地上还在发生另外两件大事——东北的“下岗潮”和海南的“地产泡沫”。
极寒之地
东北是个极寒之地。
“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山海经》中曾这样记载东北的地貌。这群在冰天雪地里饱受极寒的人,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如诗如画的描述,只能报以奢望。
再简单点说,东北人对温暖的渴求,就跟广东人想看到漫天飞雪一样,急迫又失真。这让四季有着温热气候的三亚,成了长年累月与凛冽寒冬争天抗俗的东北人心中的一块“圣地”。
虽然,如今的三亚以旅游著称,号称“东方夏威夷”。但它还有一个更为响亮、却是本地人不大乐意听到的别称——“黑龙江省三亚市”。

东北人与三亚之间的渊源,还得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当年,国企改革让东北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下岗潮”,总失业人数达到259万,占全国下岗人数的22%,一群正值壮年的东北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
下岗后,他们被迁出工厂,安置在一栋名为“职工家属院”的地方,等着国家下发的“救命钱”——补偿款和安置款。历经了一个大时代呼吸吐纳的他们,在逐渐萧条的矿区与锈迹斑斑的厂房里,思考着自己该何去何从。

一年当中,东北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冰封千里”。最冷的时候,室外温度接近零下四十度,而那些职工家属院连基础供暖设备都没有。逼仄的环境加上寒冷的侵蚀,成为压垮一部分东北人最后的稻草。
当时,他们内心只有一个想法——逃。
此时距离东北3877公里外的海南,同样在经历一场史上最严酷的“寒冬”。
那年,海南的房地产泡沫达到峰值,原本每平米售价5000元的房子,降价到300元依旧无人问津,最后变成被人用来喂猪的烂尾房。

时间如果调回到5年前,那时的海南,风光一时无两。
站在风口,猪也能飞上天。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在驶向广东湛江的火车上,这首《请到天涯海角来》回响在车厢的每一个角落。
1988年4月,海南正式脱离广东,成为中国第31个省份。
突如其来的“身份认证”让海南的发展蔚为大观,各地的商人顿时嗅到金钱的味道,他们将海南比作继深圳后的下一个淘金地。

| 摄于中国海南省成立当天
为此,当地负责人特意邀请日本专家为海南做20年发展规划,专家给出的发展方向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
20年后才能有像广州一样的经济体系?这样的发展速度明显不够。经过多方决定:房地产和旅游业,成了海南发展的优先选择。

| 三亚街头随处可见的售房信息
“要挣钱,到海南;要发财,炒楼花。”海南建省前后1年,将近10万年轻人,带着梦想从五湖四海赶到这个四季长春的海岛,其中包括之后叱咤风云的房地产大佬冯仑和潘石屹。
短短4年时间,海南房价上涨超过450%,地价上涨30多倍,形势一片大好。没人会想到,眼前这样一幅蓬勃景象会在顷刻间坍塌。
由于银根的收紧,使得200亿资金从海南撤离,须臾之间,600多栋将近16000多万平米的房子,一夜之间无人问津,最终“烂尾”。
这场狂欢,在1993年6月23日,曲终人散。曾经的繁花似锦终成了海市蜃楼。
有人悄悄退场,也有人持金而来。
“海南的房只要300块一平,而且那里还没有冬天。”这样的消息径直传到了东北。
刚下岗的东北人拿着手里的遣散费闻讯而来,在海南为自己和家人添置了第一套房产。“你不会明白一个没有冬天、永远温暖的地方,一个海鲜泛滥、有着各异水果的地方,对地处寒冷地方的人有多大吸引力。”
一传十,十传百。“海南房价便宜、气候温暖、海鲜遍布……”这些诱因从四面八方朝东北人伸出触手,促使三亚迎来了首个“南迁潮”。

| 为了吸引东北人前来购房,海南某公路上登出了定制化的房地产广告
就这样,矗立在中国一南一北的两方土地,在时代洪流的激荡下无意识地交融到一起。一边是从工业兴盛时期到消亡时期的极寒之躯;一边是一夜之间历经身价暴涨又跌落谷底的炙热胴体,两股力量相互扶持又互相排斥,在彼此成就和耗损中,同生同长。
宿命真的很玄妙。30年前,意大利普拉托的口岸迎来了第一批中国移民,怀抱发家致富的愿景和渴望;而刚刚经历“下岗潮”的东北人也正带着过去的伤痛和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海南,重新生活。
30年后,同样涌现出这样一批人,带着“不死”的韧劲。
不死的中国人
“向南,向南,直到海南!”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洗礼下,全中国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心中只有一个方向——海南。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说走就走”成了件稀松平常的事。也许早上你还在酒仙桥吃早餐,晚上就回到了位于静安嘉里的公寓中。上个世纪那种漂洋过海只为实现心中理想的情景,也许很难再见到。
直到偶然刷到一条短视频,我才发现虽然已经步入21世纪,但依然有人用最传统的方式和自己“较劲”。
最开始吸引到我的,是一位名为“徒步貂蝉(夫妻之旅)”的快手用户。
夫妻俩从成都出发,一路途径昆明、南宁、湛江、海口,最后抵达三亚。
大多数时间,妻子负责拉车,丈夫在一旁用视频记录。有时担心妻子太累,丈夫也会主动担起拉车的工作。

耗时整整71天,夫妻俩从成都走到了1672公里外的三亚。他们将一路的旖旎风光和日月星辰,都完完整整地记录在快手上。
烈日当空,车杆被晒到发烫,妻子边推车边嘀咕:太累了,太累了。

去往昭通的路上,夫妻俩遇到过暴雨,也经历过狂风。站在海拔2200米的山顶,气都喘不过来的妻子,笑着对镜头说:之后就一路下坡了,会轻松很多。

打鹰山隧道的那场大雪,见证了他们坚定的信仰,“一路上风雪交加,也阻止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一路徒步苦吗?当然苦。
路途的遥远、环境的窘迫、物资的缺乏、信念的摇摆……这些都可能成为放弃的原因,但最后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抵达昆明官渡古镇时,小两口兴奋地合影
为了找到徒步的动因,我翻找了一些资料和评论,发现他们所遭受的质疑和抨击,远比支持和鼓励要多得多。
环境改变思维方向,思维决定行为意识。就像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10年前的照片时,肯定会不自觉地发出一声:“啧!”
“审视”之前,我们不妨先抛开摘去滤镜后,曝光在光天化日下的所有不完美,思考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虐”自己?
尤瓦尔·赫拉利曾在《人类简史》中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基因是因为偶然的因素保留了下来,然后通过偶然的事件激发了某个基因,形成一个重复过程。
“这样的变异有益于生存,所以被保留了下来。之后经过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叠加,才变成我们现在的样子。”
因为一次偶然的野外徒步,让你学会应对未来某次意外事故中的自救方法;因为一次意外的迷路经历,让你发现了一家无比美味的蛋糕店……“人类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会降临,所以需要自己不断尝试、不断接触、不断创造”。
可偏偏现代人大多不愿“走出去”。
这让我想到不久前,余世存在《一席》演讲时谈到当下年轻人的焦虑,他说现在的人越来越容易陷入舒适圈,害怕挑战和改变,“(他们)都在不可知的时代命运面前让步,或者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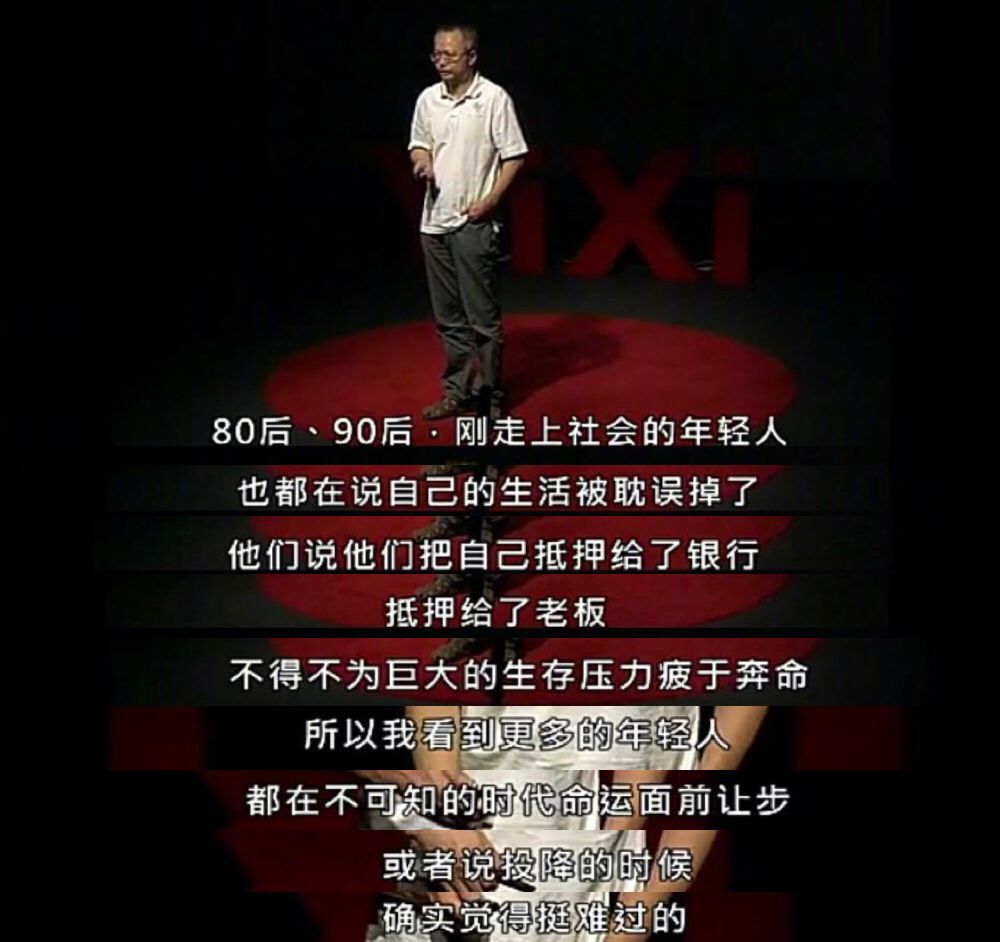
| 余世存《一席》演讲
透过这些徒步者的视频不难发现,人类关于“自我探究”的基因一直潜存,只是因为社会文明的迭代,而渐渐失去光泽。
如果温州人没有走出去,如今耸立在温州的摩天大楼需要退后多少年才能平视云端?如果东北人没有走出去,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最终会粉碎多少家庭?
如今,每天在钢筋水泥搭建的城市中穿梭忙碌的我们,也许早已忘了,繁华熙攘的城市另一边有青山有绿水,有田野有炊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或许没被生活温柔以待,但他们并没许下“请对我好一点”的美好愿景,而是用视频去记录下自己与命运抗衡的“不死”一面。
来自山东广饶,55岁的本亮大叔,在“闯入”快手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现如今,他已经拥有1357万粉丝,每条视频都能达到上百万播放量。
因为热爱唱歌,所以本亮大叔,即使不被当地人理解,他依旧没有放弃。麦子地当作舞台、拖拉机为他伴奏,还有那把捡来的旧吉他和浑厚嘹亮的嗓音,都成了本亮大叔的圈粉利器;

如果说本亮大叔凭借一腔热血到达了梦乐园,那么耿哥则是一位把理想照进现实的造梦者。
原名耿帅的“手工耿”,曾是一名北漂焊工,辞职回到老家后,他决定做一些“没用的发明”。
菜刀手机壳、雷神之锤斜挎包、一秒开瓜神器、螺母枪……耿哥的发明受到一众网友的热捧。

爆红之前,耿哥也遭受过白眼。即使家人和亲戚对他“无业游民”的身份有所抵触,但他照样坚持自己的梦想,他说,“做没用的东西,也是件有趣的事儿。”
现在快手上有200多万粉丝关注着耿哥和他的“无用的”发明,他们甚至“威胁”说:如果发明有用的东西,就取关。
在耿哥的快手主页里,那句简单的“感谢快手”,我猜应该是最能表达他情绪的一番话。
跟残酷命运肆意抗衡的人,快手上也随处可见。
“无手励志哥蒋容宇”,早年因为化学事故导致残疾。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这辈子“完了”,包括他自己。
为了生存,他曾去大街小巷卖唱,被骂过“乞丐”,也被当过“骗子”。一身狼狈回家后,他开始苦研书画,希望尽早还清家里人为了给他治病欠下的巨债。

47万粉丝、单幅画价达到38万、月收入过百万,在快手里“重生”的蒋容宇,早已告别了之前的落魄和迷惘,取而代之的是自信和顽强。
在他身上,我看到被命运无情熄灭了光亮后,试图奋力突破黑暗的力量。

| 现在,蒋容宇会偶尔以直播的方式教网友画画,他希望能有更多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中国移民登上了开往意大利的轮船,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他们省吃俭用,每天工作15个小时,只为赚到第一桶金,“隐忍、勤劳、坚韧”的品行却使他们成为意大利人口中:“不死之躯”。
若《不死的中国人》这本小说不曾出版,意大利人的偏见只会随着时间根深蒂固,而关于中国人种种的谣言,或许会成为当地人的“睡前故事”,甚至“未解之谜”。
狄更斯曾说,“这是最好的时代”。的确,互联网的飞驰发展让我们有更多的窗口,去直观地了解和触达自己周遭之外,不同人的不同生活。而不再是单一的通过书本和口传,片面想象他们的人生。
试想,如果“徒步三亚的夫妻”、“55岁的麦田歌者”、“变废为宝的焊工”、“无手的书画家”没有选择用镜头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点滴,也许他们终究只是一道来自大山深处的瑰丽传奇——没人见过,也无人问津。
过去,生活在普拉托的“不死的中国人”是意大利人嫉妒和戏谑的对象;如今,快手上这些用户,透过屏幕,被记录、被传播、被喜爱、被分享,构建成祖国疆土上斑驳光亮,展现同样的“不死”精神——前者抱有放手一搏的决心,后者拥有不破不立的信念。
最后,回到文章开篇时留下的命题——那些不死的中国人,究竟去了哪儿?
书里的中国人最后到底去了哪儿,没有人知道。但如果一定要为小说画上一个句号,我选择相信那些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拿着在普拉托赚到的第一桶金,漂洋过海去到了三亚。在着陆那一天,另外两拨人同时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他们之中,有人刚经历失业的打击,一心寻求温暖;有人带着众人的期望,只为实现诺言。
又或者,只要心中有光,似乎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不死的中国人”。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30年前,这首响彻全国大街小巷的歌曲,吸引了数以万计青年从五湖四海奔向海南;30年后,诞生于互联网的一代,以不同的躯体,从不同的方向,用相同的行为,与上个世纪的“迁徙者们”巧合重叠在一起,达成灵魂上的“不死”与“共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不知道那些“不死的中国人”会选择停在哪一帧去与命运握手言和?是徒手走进普拉托纺织市场的那天,还是三亚的阳光烫在皮肤上的一瞬,亦或是踏上远离故土的征途时,那不舍的回眸。
参考资料:
1.《“不死的中国人”: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意)欧利阿尼,(意)斯达亚诺著,邓京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董仁威:意大利的衰落与温州人之崛起》,董仁威
3.《余世存演讲》,余世存
4.《Prato, Italy: Including Its History》,Wilkins Sandra,EarthEyesTravelGuides出版社
5.《失落的温州》
6.《潘石屹五斤桔子逃生记:90年代逃顶海南地产泡沫》,侯斐
7.《人类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